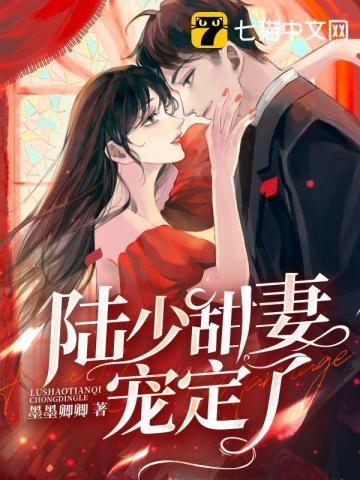盗墓小说>我在三国骑砍无双 > 第830章 高柳城破代郡收复希望之种合章6K6(第4页)
第830章 高柳城破代郡收复希望之种合章6K6(第4页)
就这样,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愈激烈,却始终拿不定主意。
眼瞅着议论陷入僵局,如此争执,恐怕难得什么共识。
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即便有个别人能保持理性,也很难说服其他人做出背叛自己屁股和阶级的事情。
这一点,也正是如今甄姜与王凌等人负责的情报局安插内应迟迟无法作的缘故。
不过现在,在外力的影响下,在关羽等人大胜的作用下,高柳城士绅们心中的坚壁还是出现了一丝裂痕。
李成当即说道:“苏曜的均田令确实让人望而生畏,但要说那科举,那可就是个实打实的善政了呀。”
众人听闻,皆是一愣,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瞬间缓和了几分,纷纷将目光投向李成,眼中满是疑惑。
“李兄,这话从何说起?这科举与我们当下困境又有何关联?””
那土财主忍不住撇嘴。
科举他知道的,京师办的考试嘛,很多太学生参与,具体他不甚了解,只听说最后闹得弘农杨氏的家主都人头落地,想来又是那贼子苏曜排除异己的手段罢了。
见有人配合,李成当即长身而起,清了清嗓子,抚须道:
“不瞒诸位所说,某家中长子求学太学,已将京中情况如实告明,这科举制,对我等幽州士民来说那可是天大的好事一件啊!”
李成的话音刚落,屋内众人顿时一片哗然。
有人皱眉思索,有人面露疑惑,还有人则直接开口质疑:
“李兄这么说,莫非是要作那贼兵们的说客?”
“这科举制不是苏曜用来打压我等世家的手段吗?怎么反倒成了好事?”
李成微微一笑,环视众人,缓缓说道:“诸位有所不知,科举制虽说是苏曜推行,但其本质却是为天下士子开辟了一条上升之路。”
“以往察举制下,世家大族,尤其是那些关东世家们垄断仕途,寻常学子即便有才,也难有出头之日。”
“就如我等边郡子弟,即便数代积累,也不过困于一隅之地,世为郡吏,难有作为。”
“而如今,苏曜这科举制一出,那不论出身,唯才是举,这对我等边郡士民来说,岂不是天大的机会?”
“机会?”
有人冷笑一声,“李兄莫不是被那苏曜蛊惑了?科举制虽说是唯才是举,但那些考题、考官,还不是被世家大族掌控?我等边郡士民,如何能与中原世家抗衡?”
“此言差矣!”
李成摇了摇头,正色道:
“诸位可知,此次科举,三甲之中有两人皆是寒门出身,其中一人更是来自边郡扶风的不知名之辈。”
“这说明什么?说明苏曜的科举制并非虚设,而是真正为天下士子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况且,”
李成继续说道,“苏曜在科举制中特意为边郡士子划定了名额,确保我等边郡士民也能在科举中占得一席之地。这等举措,难道不是对我等边郡士民的优待?”
屋内众人闻言,纷纷陷入沉思。
李成的话确实让他们心中有所触动。
以往他们作为边郡士民,仕途上总是被中原世家压制,难以出头。
如今科举制一出,似乎真的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可是……”
那土财主依旧不甘心,皱眉道,“即便如此,苏曜的均田令又如何解释?他若是真为我等边郡士民着想,为何又要推行这等损害我等利益的政令?”
李成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均田令确实触及了我等的利益,但诸位不妨换个角度想想,苏曜推行均田令,目的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缓解百姓的困苦。”
“如今天下渐乱,那是流民遍野,反贼遍地,多少豪门大户毁于战火,数代积累付之一炬?”
“倘若大将军的政策真能够使得天下大治,让百姓能安居乐业,令社会安定,我等又何尝不能从中受益?”
“再者,”
李成顿了顿,继续说道,“苏曜虽推行均田令,但也并非一味打压我等,还是允许保留一定数量土地的,其更多的还是限制那些豪门巨富。”
“按他的标准要求来看,以某之间,实际上再在座各位受到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只要我等遵纪守法,不再肆意兼并,便不会受到过多影响。”
“况且,苏曜还推出了特许经营制,允许我等参与造纸、印刷等新兴产业,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商机啊!”
李成的话如同一记重锤,敲在众人心头。
他们原本对苏曜的新政充满敌意,但经过李成这一番分析,似乎也看到了其中的机会。
“李兄所言极是。”
赵明终于开口,缓缓说道:
“苏曜的新政虽有些激进,但也并非全无好处,我等若是固守成见,坐失良机是小,枉送性命那就得不偿失了啊。”
“赵老爷的意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