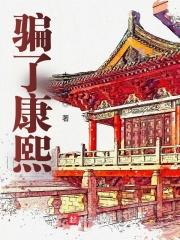盗墓小说>黜龙 > 第十三章 侠客行13(第1页)
第十三章 侠客行13(第1页)
自春日以来,东都的政治气氛便一直很紧张。
这是废话……谁家皇帝带着大半个朝堂一去不复返了;百万大军几百万民夫光走路就走崩溃了;然后大半个天下都反了,还能不紧张的?
只不过,因为洛口仓的存在,民间居然能稍微稳住,使得东都这里主要的紧张气氛依然集中在政治层面,倒显得有些令人感慨。
又或者说,在一些核心问题面前,另一些平素看起来很严重的问题,也就不算是个问题了。
“老夫来数一数……”
仲秋时分,东都紫微宫内,南衙会议堂上,好像陡然老了七八岁的相苏巍正在主位桉后尝试做一个总结。“先是最外一层,巫族西部几位小汗、小王纷纷来告,说东部都蓝可汗、中部突利可汗,一起在巫族圣山会盟……”
“不要想了,西部也无救了,隔着大漠咱们根本够不着,从今往后,西北,乃至于晋北,甚至北荒西部,自此多事了。”
东都八贵之一,兵部尚书段威面无表情地点评道。“而且,此事从西巡之后,便是定局了。”
“然后北荒也有些乱了。”
苏巍没有多嘴,只是继续坐在那里进行盘点。“但事情不是什么大事,也不是什么小事,而是多事……比如于叔文过来以后,荡魔七卫便和七镇就再度闹了起来;又因为于叔文以罪身而死,上次救驾的西部几家的赏赐也都没,因此打着于叔文的旗号造了反;这还不算,观海镇的宁远伯文过来,说是北海边上忽然去了一位宗师,据说是张老夫子的爱徒,却行事激烈诡谲,强行夺地建塔,还干涉政务,旁边的巍海镇深受其苦。”
“我不知道此人。”
被周围人注视的正牌东都留守,张老夫子的幼子张世本立即摊手以对。“委实不知道。”
“我知道,刘文周嘛。”
一直闭目养神的大宗师、皇叔曹林忽然在座中睁开眼睛,认真解释。“张老夫子老早给靖安台报备过……我也大概猜到这疯子是要干嘛,但一个宗师,跑到天涯海角之地,难道要一个大宗师专门去抓?只能等他自取灭亡……就是北荒估计要被他祸害的够呛。”
“外面的事大概就是这两个,咱们接着说内里的……”
苏巍状若未闻,继续翻开一页纸来说话。
“东夷和南岭呢?东南妖族二岛呢?”
礼部尚书白横津忽然诧异开口询问。“不可能只有巫族和北荒有事吧?”
“当然不可能。”
刑部尚书骨仪正色提醒,这是一位妖族血统特别明显的人,头和胡子都黄色,眼睛一只是蓝色,却自幼生长在关陇。“但彼处事端自然要直接呈交御驾……何必一定要东都这里有说法?”
白横津状若恍然,立即闭嘴。
“外面是两件大事,内里则有三件大事。”
苏巍继续对着手中文书言道。“一来是陛下有旨意,着紫微宫宫人、内侍、金吾卫护卫皇后与诸妃嫔、公主,一并送往江都随驾……”
没有人吭声,大家去看曹皇叔,后者也只是继续闭目不语。
“二来,是江东、荆襄、巴蜀那边函,说有圣旨到,要求秋后税赋顺江而下,交江都使用,不再转入关中与沿大河诸仓……”
还是没有人吭声,曹皇叔倒是终于二度睁开了眼睛。
“三来,是秋后,东境、河北、中原、江淮,连着之前说的北荒,还有晋北,一共三十七个郡、镇、州、卫,报了盗贼、灾荒,要求减免税赋、贡物,其中十五个州郡直言,如果不能剿灭盗匪,秋税是没法递交的……少数几个郡,甚至说,如果朝廷再不剿匪,他们只能一死报国报君了。”
苏巍念完,将一大摞表格、文书摊开,放在了自己身前桉上,再来看众人:“这是具体各郡的情况……都已经整理好了,诸位想看自己来拿。”
然而,没有人动弹,也没有人吭声,而堂内诸位贵人的目光,反而愈集中看向了座中一人。
那人,也就是皇叔曹林了,沉默片刻,倒也干脆:
“我先说吧!攘外必先安内,巫族那里派个使者去突利可汗那里做个样子便可,东部中部虽然结盟,可如何去并西部,如何分润部落,两家不是那么好办的,我估计也要争个高低才行……更别说,西北各塞堡仍在了,也就是晋北稍微麻烦些。但也有白公在那里……真正巫族大统,大举南下,最少也要三五载……此事先放一放。”
众人纷纷颔,不然还能咋地?
“北荒那里,表面上是内务,其实是外伤,大家心里都明白的,荡魔七卫跟七镇折腾了好几百年,不差这一回……刘文周的事情刚刚就说了,实在是没办法……也只能派个使者安抚一下宁远伯他们,然后让幽州诸州郡尽量与七镇做个协调照应。”
曹皇叔继续做着决断。“而且我说句不好外传的话,为什么不给宁远伯一个东部镇守或者西部镇守的名义?为什么不直接派兵助他?因为北荒那里,不怕他们闹,怕的是他们拧成一股绳,真要是合力了,甭管是素来对朝廷不满的荡魔七卫做主,还是七镇各家成了事,怕都是要往河北看的!”
其余七人也都只是颔……因为这是实在到极致的大实话。
“至于说三件内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