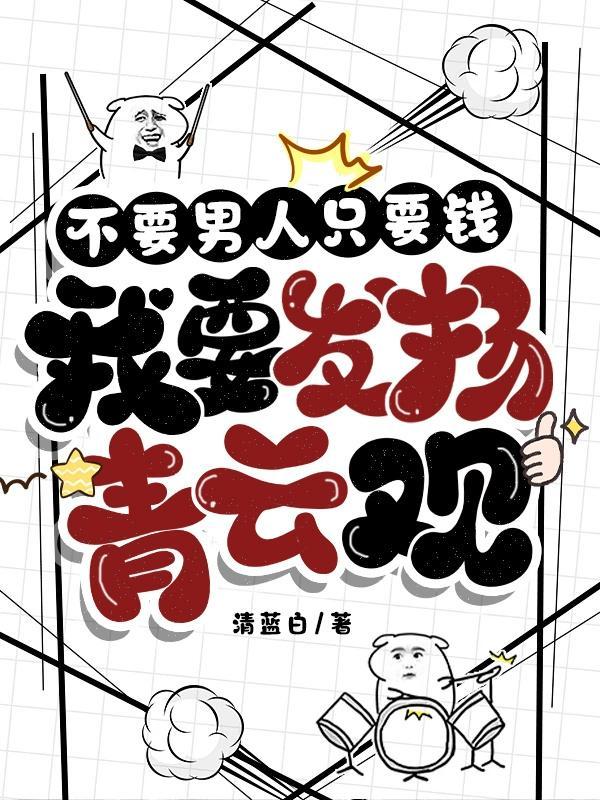盗墓小说>师妹结婚了,新郎不是我 > 第210章 将计就计(第2页)
第210章 将计就计(第2页)
瓷青釉面在烛火下泛着冷光,瘦高青年献宝似地托起酒坛。
尚未开封,坛口溢出的沉香已勾得满屋汉子喉结滚动。
当红绸封泥碎裂的瞬间,梅子混着熟谷的醇厚气息轰然炸开,几个莽汉竟不自主向前探出脖颈。
“猴儿酿!”
靠窗的疤脸男从牙缝里挤出惊叹。
这种用未熟青杏窖藏三年的烈酒,向来只在江南花船上流通。
黑脸大汉指节叩着案几,陶碗相碰声立刻响成一片。
二蛋执坛穿梭如游鱼,琥珀色酒液在粗陶碗里激起细浪。
当最后一道酒线注入黑哥海碗时,角落里突然传来陶器碎裂声——有个红脸汉子竟醉得把碗啃掉半块瓷边。
铜壶滴漏转过三刻,木门吱呀推开时,浓烈酒气凝成可视的雾团。
楚阳靴尖踢开挡路的空坛,目光扫过满地瘫软的躯体。二蛋垂手立在阴影里,后颈还沾着故意泼洒的酒渍。
“东西收了?”
“按您吩咐,都在这了。”
青年袖中传出玉瓶轻碰声。
楚阳突然逼近半步,指尖白丹在对方瞳孔映出两点寒星:“含香丸需用舌尖抵着化开,记住了?”
见二蛋颌骨绷紧却不敢躲闪,他忽然轻笑:“现在该醉了。”
酒坛应声倾倒,青年仰头时喉结剧烈颤动,几滴清液顺着下颌滑进衣领。
当啷一声空坛坠地,二蛋踉跄栽进酒泊的姿态,竟比真正醉汉还要狼狈三分。
碎瓷声炸响厅堂,二蛋冲楚阳扯出个痴笑,脖颈突然失了支撑般重重磕在桌沿。
酒碗打着旋儿滑到楚阳脚边,琥珀色液体在青砖上蜿蜒出蛇形水渍。
“三杯就醉成烂泥了?”
楚阳鞋尖轻踢醉汉肩头,踩着满地横陈的躯体走向角落。
黑面大汉鼾声如雷,布满老茧的指节上套着枚青灰铁环。
少年蹲身捏住对方拇指关节一压一旋,戒圈便滑入掌心。
神识探入储物空间时,楚阳眉梢微挑。
十平米见方的空间里,标注“壮阳丹”
的瓷瓶与粉晶雕琢的幻象玉佩挤作一团,几包催情香粉压在《春宫十八式》帛书上。
最醒目的当属三枚刻着“楚”
字的玄铁令牌,边缘还沾着未干的血渍。
“倒是周全。”
少年将令牌悬在黑汉鼻尖晃了晃,鼾声突然短促地停顿半拍。
楚阳冷笑收手,戒圈精准落回原处时,窗棂外恰好传来三更梆响。
厢房烛火摇曳,李慕白捏着茶筅正在击拂,见人回来也不言语,只将新点的茶汤推过案几。
蒸腾水雾里,他眼巴巴盯着人瞧的模样,活像书院里等着夫子糖的蒙童。
“茶沫散形了。”
楚阳屈指轻叩盏沿,任由对方抢过茶碗重添沸水,这才从袖中抖出张残破符纸。
朱砂绘制的替身咒隐约可见,符脚还粘着半片孔雀蓝衣料。
“替死鬼的戏码。”
少年指尖窜起幽蓝火苗,符咒蜷缩成灰时,窗外忽有夜枭尖啸掠过:“既有人能仿我身形,何不将计就计?那令牌的血气……”
李慕白执壶的手猛然顿住,茶汤在宣纸上洇开墨色涟漪:“你是说,凶手在故意标记犯案时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