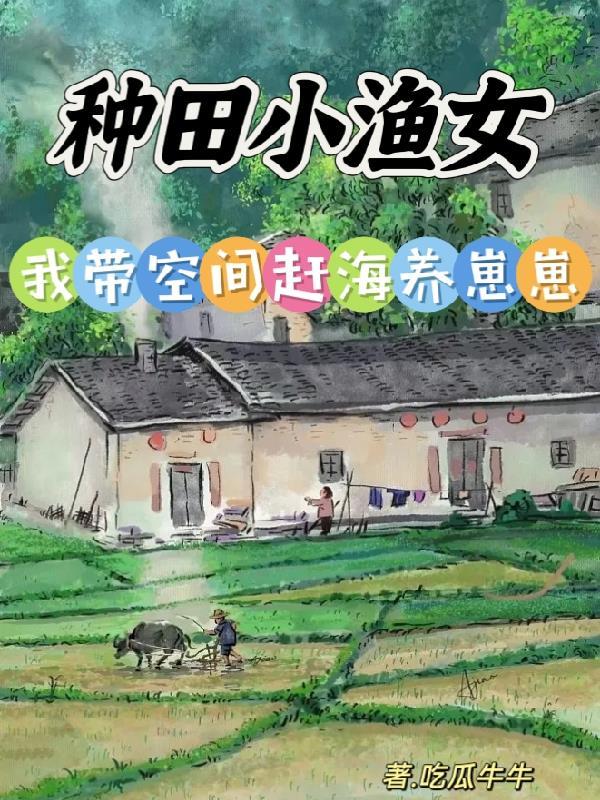盗墓小说>一梦是谁 > 第3章 逃命永平府(第2页)
第3章 逃命永平府(第2页)
队伍度很快,没有人催促,兵丁们自扬起鞭子,驱使骡马加快步伐,相互鼓劲。
队伍中间的一辆平板架车上,躺着一个青年,身上盖着被子。
道路颠簸不平,车夫尽力的掌握着车身和骡子,走平缓的路面。
驾辕另一处坐着一小青年,照看着躺在车上的人,不时的拉拽着被颠簸抖开的被子。
行进点距永平府三十里的地方,午时已过人累马乏队伍的度降了下来,纷纷拿出来早上分的干粮,边走边啃食起来。突然远处飞奔疾驶来一侦骑:
“敌袭!敌袭!”
本来就不整齐的队伍变得更混乱起来,亲兵们纷纷拔刀呵斥,维持着散乱的队伍。
没能用辎重大车组成防御工事,远处已经阵阵尘土飞扬,传来了急促的“哒哒哒哒哒哒”
马蹄声。
鞑子骑兵转瞬即到,无奈陈汉秋只能组织阻击,为突围争取时间。
几个年轻人,冒着鞑子骑兵的箭雨,催促着马夫赶车脱离大队,朝永平城的方向疾驶。
战场上的惨叫声此起彼伏,声音越来越低,一行人离战场越来越远。
因为鞑子骑兵的肆孽,官道上几无人烟,只有北方在吹打着干裂的树枝和野草。
小半个时辰后,永平府城的轮廓,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里。
陈邵叫停了战马,对着大家说道:
“文抚和柱子照顾少爷进城,我们回去接应老爷。”
陈文抚点点头说到:
“千万小心!”
看着几个人调转马身,朝来时的路上疾驶而去,陈文抚二人驱赶马车,来到了城门外。
…………
陈修远高烧昏睡了一个多月,永平府的大夫都找了遍,各种药方都有尝试,就是不见效果。
一早,陈文抚就又去请大夫了。
床上的陈修远,今天开始有了些意识,耳边隐约听到两个人在唉声叹气说话,
“少爷这么长时间不醒咋办啊?”
另一个道:
“忠叔正在为少爷袭职百户的事跑门路,花了那么多银子,唉!不花这银子,我们跟着忠叔回老家多好。”
“你咋这么没良心,老爷对我们那么好,没有老爷你早就饿死了,少爷虽然没有醒,但是少爷没死,你怎么说那么缺德的话,难道你想扔下少爷回老家?”
“你胡咧咧个啥!我啥时候说扔下少爷了,我扔下少爷?你看!”
边说他边扯开衣服,胸膛上露出两处刚愈合的刀口,左臂上还有一个箭伤。
“跟着邵哥、老爷和东虏拼命时我退缩过吗?邵哥和老爷都没了……”
说着说着他眼圈红了。
“听老爷在世时说过,那些个当大官的贪人钱财,心黑的狠,我怕他们收了钱不办事,还不如带着少爷回老家去,买上等的药材医治少爷。”
“朝宗哥你别难过了,我以为你要学李正他们呢,丢下少爷攀高枝去。”
“别提那些个白眼狼,老爷对他们恩重如山,视若家人,老爷刚去逝尸骨未寒,便做出背弃陈家的事来!”
两个人来言去语断断续续飘进陈修远的耳朵,这些天一直靠参汤补药将养身子,使他感觉口干舌燥,努力的张张嘴想说“渴死我了,让我喝点水,”
但最终只说出了个“水”
字。
两人好像没听见,还在说着话,陈修远使出吃奶的劲又说了一个字“水”
这一个水字打断了两个人的谈话,同时扭过头来看床上的陈修远,只见他们少爷已经睁开了眼睛,头努力的向外偏了偏看着他俩说到: